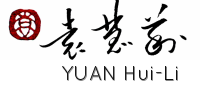ACT 藝術觀點 雜誌 第87期專訪 2021.10
袁慧莉Yuan Hui-Li—2021訪談錄
訪談單位──ACT藝術觀點編輯部
訪談日期──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下午四點
訪談地點──金山畫室
受訪者──袁慧莉
訪談者──李佩姍、宇田奈緒
錄音──李佩姍
刊登媒體──ACT藝術觀點第87期2021年10月出版,頁66-75。
以女性為主體建構的山水畫
李佩姍(以下簡稱「姍」)──老師能不能談談這次在耿畫廊的個展「隱身皴」,從一個女性主體意識出發,觀察中國山水以男性主體建構的歷史。像這次個展,自己身為女性藝術家,在這個時代裡,對於山水部分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袁慧莉(以下簡稱「袁」)──中國山水畫歷史大部分是以男性為主,女性非常少。古代女性做山水畫,通常是偏向男性建構的山水畫風格為主。在歷史裡面,從女性角度提出來的山水圖像和論述很少,因為山水畫論述多是男性書寫。我認為現代女性已撐起半邊天了,也該要有自己的角度、觀點,或從女性情感視角賦予山水畫跟過去不一樣的樣貌。
姍──這樣來說,提到「隱身」這樣的說法,會帶有陰性書寫的部分嗎?
袁──基本上,隱身的「隱」有兩個含義,一個是隱喻,一個是隱藏。隱藏的部分就是我把情緒隱藏在山石裡面;而隱喻,則隱含了主體性與主體政治。「身」,身體的身,也就是「身」為女性主體,我有什麼樣的看法,我這個主體跟歷史中的男性主體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要講主體性?事實上,古典山水畫史跟男性主體與其主體政治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作為一種繪畫的類型,山水畫不只是山水而已,也不只在講自然的樣貌,它也是主體話語權的競爭場域,這就是一種主體政治的特徵。我研究過往中國的山水畫家,大部分都是識字文化人,具有話語、書畫表述能力的文人,或掌握著社會話語權的政治人,基本上,他們往往寄託政治觀點或自身思想在自然山水圖像之中。山水畫因此可能是一個主體他要透過山水畫裡的所有物件展現出他的自然觀或人生思想的場域。或者如果是院畫家畫山水畫,例如北宋郭熙,他就在山水畫裡歌頌他的老闆也就是宋神宗這個君王主體,將宋神宗的政治主體隱喻在「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的山水結構中,所以山水畫不只是自然風景,後面還隱藏著主體政治意涵。
不過,古典山水畫裡的「皴」大部分還是作為指涉自然肌理的造型物件之一,並未被獨立出來。我跟古典山水畫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將「皴」抽離出來,將主體所要隱喻的思想與情感,透過「皴」來展現,並且以情緒性的意指方式重新詮釋「皴」的定義,從這個角度看,就是顛覆傳統符號的語意觀,使「皴」脫離過去男性給予的自然性詮釋定義,使「皴」從「師自然」的客觀性,轉向全然「得心源」的主觀性,這不是造型上的抽象山水畫,而是意涵上的山水抽象化。而剛好我身為女性,可以展現這種脫離男性話語宰制包袱的自由。
《類山水No.43》,66x133cm,洒金淨皮宣、彩墨,2015
《類山水No.46》,66x133cm,洒金淨皮宣、彩墨、泥金,2015
山水畫的政治性
姍──所以作品中的山水把它比喻成一個主體,「類」是否代表了它的政治性?或者為什麼使用「類」這個字?
袁──先講「類」這個字的來源,《山海經》裡《南山經》第一篇就有「類獸」。所謂的類獸就是陰陽同體、混雜體。牠是很難被分類的,因為牠既陰也陽,牠是雌雄同體。牠本身已經具足了二元,打破了二元對立,融合二元的差異並置,《山海經》賦予牠叫做類獸,就是因為牠難以被分類。為什麼我要挪用「類」來命名我的山水畫?因為我這批作品在談的是,一個女性主體以自身觀點,突刺進入男性山水畫史所建立的話語場域之中,進行內部的差異並置,我的《類山水》作品開始展出十幾年來一直常聽到觀者說看不懂,就是因為觀者想從舊有的認識論路徑去分析和解讀,往往很難對上。《類山水》將過往的自然性山水變成情緒性山水,沒有客觀的物件可以對照,看似傳統的山水畫圖像,細看卻大相逕庭,其內涵與意義更是大不相同,頗讓觀者困惑,直到今年個展發表《袁氏皴譜》,《類山水》才被理解。同時我也將過往山水畫習慣以皴作為統攝畫面一致性、協調性風格的角色,變成複雜多樣的「皴」,使畫面的結構趨向差異並置狀態而非一致性,所以,使用「類獸」的「類」就是在隱射這種差異並置、當代多元主體政治特徵的隱喻。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有著自由民主的政體,可以有不同意見的發聲,因此是個眾聲紛雜差異並置的世界。《類山水》就是要講這樣的當代多元主體政治現象。透過「皴」,每一個「皴」既是一種情緒話語,也隱喻著一種聲音,並置一起就形成了熱鬧而混雜的世界。
姍──那是否同意說要解構過去傳統山水畫的政治語言?
袁──現在不是封建時代,也不是專制社會,自由民主政體就要有自由民主政體眾聲雜沓特徵的山水圖像。所以我也以動態影像的《類山水Ps.早春圖》去表達現代山水圖像取代古典山水的概念,這件單頻道錄像作品就是在講政治主體的古今變異。
《類山水No,49》,49x228cm,灑金淨皮宣、彩墨,2016
《類山水PS.早春圖》投影現場,尺寸依場地,單頻道錄像,2021
袁氏皴譜
姍──可以談談《袁氏皴譜》,是怎麼樣去鋪陳這些多種的類型?
袁──這次《袁氏皴譜》提了三十二種皴,當然原來更多。第一版、第二版都沒有展出,因為那都是我的過程。找出比較有特色的,或是不要太重複的,就有三十二種皴。每一種皴的發生都跟我個人的生命經驗及情緒很有關係,所以那並不是刻意產生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的。雖然我很早就決定要從皴這個議題去探討,很早就開始研究,可是我要用什麼方式、形式去討論這樣的議題,一開始並不知道的,直到二〇〇七年剛好跟我當時的精神狀態相配合,一開始是無意識的塗鴉,然後想將當時的情緒直接抒發出來,從思念、悲傷、憤怒到比較混亂的心情,都變成筆下的各種皴的樣子。 等畫了十幾年之後,我開始整理回頭看,才知道我情緒的狀態,在不同的時段發生了不同的變化。有時候我覺得畫畫是一種治療,你的精神狀態是什麼就會是什麼,它會反映你的精神狀態,越到後面那個情緒的變化會慢慢舒緩下來,所以這樣的一個轉變,我覺得它就好像人的十幾年來的情緒,在不斷重複中存在著多樣性。
姍──像是生命週期有高低起伏這樣?
袁──對。就是說當某些事情發生,當下剛開始的時候你會很激烈,當時間治療到最後會比較和緩,我覺得這個東西要被整理出來,所以說我已經畫了很多了,才開始著手做皴譜的整理。一方面我也想透過皴譜這個形式去解構《
芥子園畫譜》 ,《芥子園畫譜》 是中國畫的歷史,被歸納整理具體的代表著作,拿來形式的挪用,再把裡面的語言都改編掉了,這就好像將自己女性的意識置入男性畫語世界裡,把裡面的意思改動,看起來好像古典,其實全部變成另一種話語意涵。
宇田奈緒(以下簡稱「奈」)──我比較對於情緒變成行動感興趣,那個畫畫的過程是一個自我治療?
袁──對。一開始是一張白紙,我就開始想,當下是什麼,想什麼就畫什麼,然後自己也不知道,沒有草稿。
奈──有一個像石頭,一個一個一點一點獨立出來的。有一個有顏色,有一些是白色,是因為情緒?
袁──對。顏色在畫中的存在沒有一定,但其中有兩個特殊的顏色,紅色的和留白的,紅色的代表女性經血的符號,留白則是代表內心被挖空的感覺,後來也隱喻給彼此留一個餘地,什麼都不說,也挺好的。我一開始是用金色作底,那是因為以前情緒是需要濃烈的顏色,我那時候去過太湖,太湖夏天的水黃澄澄的,我看到像黃金一樣的太湖,那時開始畫《類山水》的時候取名叫《太虛系列》,大部分都是泥金底色。
奈──像蘇州,太湖霧茫茫的,有太湖石。
袁──你知道元代王蒙他畫了一幅畫《具區林屋》,就是畫太湖西山島石公山林屋洞。我去那個林屋洞玩,在想如果傳統的男人這樣畫,我該怎麼去畫跟他們不一樣的皴。透過皴這件事情來思考,他們已經發明了什麼皴什麼皴,我也來發明什麼皴。
奈──後來就是創作《類山水》的各種皴?然後後來分類出三十二種形成《袁氏皴譜》。
袁──對。
奈──《袁氏皴譜》裡面有文字。
袁──文字很多,內容其實很片段。有詩、現代詩、詞,沒有一定格律的寫法。
奈──寫的時候跟畫畫有一定的...
袁──對應。
袁──你知道為什麼用這種形式嗎?因為《類山水》的圖像本身,已經有點抽象性了,所以如果沒有文字來說,可能沒有人知道在說什麼,文字是輔助,作為詮釋去理解。文字在皴譜來講,是必要的存在。就像是解讀《類山水》裡山石意涵的索引。
姍──想要請問老師的《類山水》作品很多都是金色的底,因為我之前有到唸到佛經,說有說金沙布地,那這個跟佛經的典故有關係嗎?
袁──沒有關係。我剛有講說這跟太湖有關。我們畫家是視覺動物,視覺做引導,當時給我的影響是,太湖水面波光粼粼的光,而夏天的光是金色,所以顏色是用金色來表現。跟浮世繪、佛經沒有關係,主要是感知經驗,與視覺的感知經驗有關。
姍──視覺的感知經驗去創作的手法?
袁──對。譬如我一九九二年開始在金山地方住,這個地方冬天多霧潮濕,白色的景象就會比較多,所以我早期一九九二年搬來這邊,開始受到這邊環境的影響,作品會偏比較淡,比較白。現在氣候變遷比較沒那麼多水氣,但是這裡相對其他地方水氣還是比較多。
《袁氏皴譜:書名頁、序》,80.4x142.7cm,羅紋宣、水墨,2019
《類山水No.58》,六件一組,49.9x57cmx6p,總長149.7x171cm,彩墨宣紙,2018
墨的兩種呼吸方式
姍──另外我滿好奇《火墨》系列作品,可以跟我們談談你在創作的過程,怎麼樣想到用這個方式作為水墨畫表現?
袁──主要是2015年去北京的時候,去的第一天就霧霾紫爆警報,一下飛機就開始戴口罩。我是屬於比較敏感的體質,北京這個空氣的味道,還有氛圍對我影響很重,因為一落地就開始咳嗽咳不停。。那個時候空污實在是太鋪天蓋地了,沒辦法忽略它,已經形成國家級警報了,你就會正視這個問題。二十一世紀地球暖化,空氣污染造成氣候變遷,未來我們會常常遇到。我就開始關心這個。那時候是去交流活動,我們要做一些現地創作,本來要拿「類山水」去展覽。到那邊就改變,改做跟空氣有關的題材。在北京我就在思考怎麼去因應這個空氣議題,又不能脫離自己是山水畫家,以山水畫這種傳統文化脈絡去對應這種新的山水狀態,所以想到用宣紙。水墨用的墨條來自於燒木頭取炭灰,調膠做成墨條,加水就能畫。宣紙同樣是來自於樹、樹皮,經過水的過程,泡軟打漿。它的原料跟墨條是一樣的,都來自於樹,一個是經過火取炭、一個經過水調製、打漿。既然原料一樣,我就把它還原。把它燒了再還原回到炭的狀態。宣紙作為山水畫常用的媒材,我將宣紙改為畫火墨的炭灰來源,以取代水墨的墨條進行作畫,這可以說是一種觀念藝術,是從物質的文化屬性來進行傳統工法的解構。它呼應著山水畫裡的物性脈絡,在對比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差異,也同時提出文化物質工法的新舊辯證關係。同時,在對應時代流轉後的氣候變遷現象時,也是透過同樣材質的差異表現,清晰地展現這個古今變遷現象。我在想古畫中的空氣總是美好的,而今空污的差異性,就要找古畫裡足以代表空氣美好、滋潤水墨的山水圖像作為臨摹對比的對象,用「火墨」去臨摹水墨作品,藉此強調氣候變遷與時代變異。 所以用宣紙的炭灰直接對臨古畫,這是完全以「火墨」的燥性所代表的空污霧霾對比古典水墨山水畫裡氤韻華滋的潤墨。過程中不加任何水,也不加膠,不用膠去固定它,讓它在宣紙上自由地飄動,象徵霧霾微粒在空氣中飄動的樣子。
姍──原始的狀態?
袁──宣紙燒出的炭灰,畫在宣紙上,它們是同材質、同質性的東西用手去畫。畫完黏著在上面,要掉就掉。在二〇一七年「墨的兩種呼吸方式」個展,我主要就是提出墨的兩種方式:水墨與火墨進行所謂墨性語言的物性辯證,它是材質性的辯證,同時也是材質背後所代表的古今美學觀點的對辯。當代的山水畫美學不見得要完全依循傳統美學,有時候需要從傳統的反面去帶出古今差異之處。過往傳統水墨背後的美學語言都要潤墨,所謂渾厚華滋、墨瀋淋漓,都是要表現水氣很美好的那種墨韻感覺。但是我用「火墨」,它反而在強調燥墨,燥墨要對應的是氣候乾燥、野火災難、在空中飄散的pm2.5空污微粒,而不是潤墨,這是古今氣候變異下所產生的美學語言變異。把傳統沒有表現過的反面的東西顯現出來,古典山水畫總是要追求或表現美好的桃花源、理想世界這樣的概念,但在二十一世紀空污氣候的當代,這樣的美好理想世界,因為空氣的問題,或許反而成為對當世一種再也回不去的嘲諷。因為氣候變異、暖化空污所造成的影響,美好理想的空氣會慢慢消失。用燥墨、火墨去對應潤墨其實也在講古今自然的變異。二十一世紀地球氣候變化太大,「火墨」發生在現在,是反映了如今真實的世界樣貌。
姍──像現在是疫情的年代,這個議題會放進你的創作裡嗎?
袁──創作前提是我要有感覺,目前還沒有感到這個議題需要我來做。。
姍──我感覺創作環境對你很重要。
袁──我所經歷的感知會去反映在創作裡。山水畫從古代就開始談「真山水」,但什麼是真山水?每一個時代都有談什麼是真。有人認為的「真」是表現親眼所見,對我而言,「真」不只是肉眼的,也是身體感知的,更是精神上所感受的。創作者面對自身真實所經歷的,不為了符合傳統美學而去逃避自身真實的感受,即使與他人或古典美學說的是不一樣的話,也勇敢地真誠表達。
姍──我滿好奇你探討水墨真實的本質是什麼東西,就像火墨這樣子。像它們本來都是同樣的東西,它們之所以不同,在於它們介質的改變,而讓它們成為一件作品,是對於本質探索的問題或見解?
袁──《火墨》探討的是我們如何透過重新看待墨的物性本質,去實質地將這些文化物質作為我們創作上表達的工具,而不是被傳統的使用方法所限制,這是跳過歷史眾相的文化侷限,回到創作自身語言所需去重新使用材質工具,並且重新定義、詮釋,賦予舊的物質新的觀點與美學語言。水墨沒有所謂真實的本質,因為我認為創作該有的自由在於不役於物,「物」不管是物質的或者性質的,都不應該被限制在單一的文化邏輯中。所以我喜歡拆解過往已被定型的概念。《火墨》拆解的是墨的物性,《類山水》拆解的是「皴」的形意語言,我的另一個系列《時間之漬》同樣也是在拆解,拆解的是傳統水墨常使用的「積墨法」,把原來「積墨法」的積墨而厚重,變成積墨而輕透。這是在材質與技法之間探討新的關係,是有關時間的觀點,而不只是在談筆墨美學而已。過去積墨法主要是在談筆墨造型美感,而我則運用現代攝影製作成影像,將積墨法裡的時間特性拉出來彰顯。
《墨的兩種呼吸方式》個展裝置一景,2014
《火墨.許道寧秋山漁艇圖》,畫作49x210cm供桌W100xH80xD30cm,宣紙炭灰於宣紙、灼宣紙卷裝置於白色供桌上, 2017
舞山水
袁──二〇〇七年間,不是只有《類山水》,我還有一個系列叫《舞山水」。《舞山水》是沒有草圖,將紙鋪在地上,不是桌上。用整個身體跳躍去運動,是一種情緒的直接反應。那個舞山水的畫是很大張,只用線條。那個線條就是當下的直覺性,身體表達內在的情緒狀態,透過手指去表達出來,大部分都是用紅色的硃砂和硃膘顏色畫線條,我當時尚未接觸西方的「陰性書寫」理論,但直覺就是要用類似經血的顏色來畫。那種畫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就是它更直覺性。所以那個畫很多,但最後只剩下七張拿出來展,其他都不行。
奈──所以創作是自我療癒,會想到給別人看到,這個是很大的不同?
袁──在畫的時候只關注自己,並沒有想給別人看,那就是一種抒發,畫完了,有人來看,覺得不錯,願意幫忙展出,就展示出來。不過,我也會在不同系列裡去探討水墨畫的一些歷史問題,並且將這些思考混合在感性之中,用自己的想法表述出來。
《舞山水之流形生發系列No.1-7》裝置現場,232x50cmx7件,淨皮宣卷軸、硃砂、泥金、礦物顏料, 2010
《時間之漬 No.6》,134x66cm,蟬翼宣彩墨,2007-2017
袁慧莉簡介
袁慧莉1963年出生於台北,曾以袁澍、袁漱別名發表作品。1987年畢業於第一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水墨組,2005年取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碩士,2016年獲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士學位。創作結合傳統水墨歷史思考與當代多元新觀念而別出蹊徑為特色,被視為台灣戰後現代水墨發展史第三代中極具代表性的當代水墨畫家之一。現為耿畫廊經紀藝術家、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訪談單位──ACT藝術觀點編輯部
訪談日期──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下午四點
訪談地點──金山畫室
受訪者──袁慧莉
訪談者──李佩姍、宇田奈緒
錄音──李佩姍
刊登媒體──ACT藝術觀點第87期2021年10月出版,頁66-75。
以女性為主體建構的山水畫
李佩姍(以下簡稱「姍」)──老師能不能談談這次在耿畫廊的個展「隱身皴」,從一個女性主體意識出發,觀察中國山水以男性主體建構的歷史。像這次個展,自己身為女性藝術家,在這個時代裡,對於山水部分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袁慧莉(以下簡稱「袁」)──中國山水畫歷史大部分是以男性為主,女性非常少。古代女性做山水畫,通常是偏向男性建構的山水畫風格為主。在歷史裡面,從女性角度提出來的山水圖像和論述很少,因為山水畫論述多是男性書寫。我認為現代女性已撐起半邊天了,也該要有自己的角度、觀點,或從女性情感視角賦予山水畫跟過去不一樣的樣貌。
姍──這樣來說,提到「隱身」這樣的說法,會帶有陰性書寫的部分嗎?
袁──基本上,隱身的「隱」有兩個含義,一個是隱喻,一個是隱藏。隱藏的部分就是我把情緒隱藏在山石裡面;而隱喻,則隱含了主體性與主體政治。「身」,身體的身,也就是「身」為女性主體,我有什麼樣的看法,我這個主體跟歷史中的男性主體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要講主體性?事實上,古典山水畫史跟男性主體與其主體政治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作為一種繪畫的類型,山水畫不只是山水而已,也不只在講自然的樣貌,它也是主體話語權的競爭場域,這就是一種主體政治的特徵。我研究過往中國的山水畫家,大部分都是識字文化人,具有話語、書畫表述能力的文人,或掌握著社會話語權的政治人,基本上,他們往往寄託政治觀點或自身思想在自然山水圖像之中。山水畫因此可能是一個主體他要透過山水畫裡的所有物件展現出他的自然觀或人生思想的場域。或者如果是院畫家畫山水畫,例如北宋郭熙,他就在山水畫裡歌頌他的老闆也就是宋神宗這個君王主體,將宋神宗的政治主體隱喻在「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的山水結構中,所以山水畫不只是自然風景,後面還隱藏著主體政治意涵。
不過,古典山水畫裡的「皴」大部分還是作為指涉自然肌理的造型物件之一,並未被獨立出來。我跟古典山水畫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將「皴」抽離出來,將主體所要隱喻的思想與情感,透過「皴」來展現,並且以情緒性的意指方式重新詮釋「皴」的定義,從這個角度看,就是顛覆傳統符號的語意觀,使「皴」脫離過去男性給予的自然性詮釋定義,使「皴」從「師自然」的客觀性,轉向全然「得心源」的主觀性,這不是造型上的抽象山水畫,而是意涵上的山水抽象化。而剛好我身為女性,可以展現這種脫離男性話語宰制包袱的自由。
《類山水No.43》,66x133cm,洒金淨皮宣、彩墨,2015
《類山水No.46》,66x133cm,洒金淨皮宣、彩墨、泥金,2015
山水畫的政治性
姍──所以作品中的山水把它比喻成一個主體,「類」是否代表了它的政治性?或者為什麼使用「類」這個字?
袁──先講「類」這個字的來源,《山海經》裡《南山經》第一篇就有「類獸」。所謂的類獸就是陰陽同體、混雜體。牠是很難被分類的,因為牠既陰也陽,牠是雌雄同體。牠本身已經具足了二元,打破了二元對立,融合二元的差異並置,《山海經》賦予牠叫做類獸,就是因為牠難以被分類。為什麼我要挪用「類」來命名我的山水畫?因為我這批作品在談的是,一個女性主體以自身觀點,突刺進入男性山水畫史所建立的話語場域之中,進行內部的差異並置,我的《類山水》作品開始展出十幾年來一直常聽到觀者說看不懂,就是因為觀者想從舊有的認識論路徑去分析和解讀,往往很難對上。《類山水》將過往的自然性山水變成情緒性山水,沒有客觀的物件可以對照,看似傳統的山水畫圖像,細看卻大相逕庭,其內涵與意義更是大不相同,頗讓觀者困惑,直到今年個展發表《袁氏皴譜》,《類山水》才被理解。同時我也將過往山水畫習慣以皴作為統攝畫面一致性、協調性風格的角色,變成複雜多樣的「皴」,使畫面的結構趨向差異並置狀態而非一致性,所以,使用「類獸」的「類」就是在隱射這種差異並置、當代多元主體政治特徵的隱喻。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有著自由民主的政體,可以有不同意見的發聲,因此是個眾聲紛雜差異並置的世界。《類山水》就是要講這樣的當代多元主體政治現象。透過「皴」,每一個「皴」既是一種情緒話語,也隱喻著一種聲音,並置一起就形成了熱鬧而混雜的世界。
姍──那是否同意說要解構過去傳統山水畫的政治語言?
袁──現在不是封建時代,也不是專制社會,自由民主政體就要有自由民主政體眾聲雜沓特徵的山水圖像。所以我也以動態影像的《類山水Ps.早春圖》去表達現代山水圖像取代古典山水的概念,這件單頻道錄像作品就是在講政治主體的古今變異。
《類山水No,49》,49x228cm,灑金淨皮宣、彩墨,2016
《類山水PS.早春圖》投影現場,尺寸依場地,單頻道錄像,2021
袁氏皴譜
姍──可以談談《袁氏皴譜》,是怎麼樣去鋪陳這些多種的類型?
袁──這次《袁氏皴譜》提了三十二種皴,當然原來更多。第一版、第二版都沒有展出,因為那都是我的過程。找出比較有特色的,或是不要太重複的,就有三十二種皴。每一種皴的發生都跟我個人的生命經驗及情緒很有關係,所以那並不是刻意產生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的。雖然我很早就決定要從皴這個議題去探討,很早就開始研究,可是我要用什麼方式、形式去討論這樣的議題,一開始並不知道的,直到二〇〇七年剛好跟我當時的精神狀態相配合,一開始是無意識的塗鴉,然後想將當時的情緒直接抒發出來,從思念、悲傷、憤怒到比較混亂的心情,都變成筆下的各種皴的樣子。 等畫了十幾年之後,我開始整理回頭看,才知道我情緒的狀態,在不同的時段發生了不同的變化。有時候我覺得畫畫是一種治療,你的精神狀態是什麼就會是什麼,它會反映你的精神狀態,越到後面那個情緒的變化會慢慢舒緩下來,所以這樣的一個轉變,我覺得它就好像人的十幾年來的情緒,在不斷重複中存在著多樣性。
姍──像是生命週期有高低起伏這樣?
袁──對。就是說當某些事情發生,當下剛開始的時候你會很激烈,當時間治療到最後會比較和緩,我覺得這個東西要被整理出來,所以說我已經畫了很多了,才開始著手做皴譜的整理。一方面我也想透過皴譜這個形式去解構《
芥子園畫譜》 ,《芥子園畫譜》 是中國畫的歷史,被歸納整理具體的代表著作,拿來形式的挪用,再把裡面的語言都改編掉了,這就好像將自己女性的意識置入男性畫語世界裡,把裡面的意思改動,看起來好像古典,其實全部變成另一種話語意涵。
宇田奈緒(以下簡稱「奈」)──我比較對於情緒變成行動感興趣,那個畫畫的過程是一個自我治療?
袁──對。一開始是一張白紙,我就開始想,當下是什麼,想什麼就畫什麼,然後自己也不知道,沒有草稿。
奈──有一個像石頭,一個一個一點一點獨立出來的。有一個有顏色,有一些是白色,是因為情緒?
袁──對。顏色在畫中的存在沒有一定,但其中有兩個特殊的顏色,紅色的和留白的,紅色的代表女性經血的符號,留白則是代表內心被挖空的感覺,後來也隱喻給彼此留一個餘地,什麼都不說,也挺好的。我一開始是用金色作底,那是因為以前情緒是需要濃烈的顏色,我那時候去過太湖,太湖夏天的水黃澄澄的,我看到像黃金一樣的太湖,那時開始畫《類山水》的時候取名叫《太虛系列》,大部分都是泥金底色。
奈──像蘇州,太湖霧茫茫的,有太湖石。
袁──你知道元代王蒙他畫了一幅畫《具區林屋》,就是畫太湖西山島石公山林屋洞。我去那個林屋洞玩,在想如果傳統的男人這樣畫,我該怎麼去畫跟他們不一樣的皴。透過皴這件事情來思考,他們已經發明了什麼皴什麼皴,我也來發明什麼皴。
奈──後來就是創作《類山水》的各種皴?然後後來分類出三十二種形成《袁氏皴譜》。
袁──對。
奈──《袁氏皴譜》裡面有文字。
袁──文字很多,內容其實很片段。有詩、現代詩、詞,沒有一定格律的寫法。
奈──寫的時候跟畫畫有一定的...
袁──對應。
袁──你知道為什麼用這種形式嗎?因為《類山水》的圖像本身,已經有點抽象性了,所以如果沒有文字來說,可能沒有人知道在說什麼,文字是輔助,作為詮釋去理解。文字在皴譜來講,是必要的存在。就像是解讀《類山水》裡山石意涵的索引。
姍──想要請問老師的《類山水》作品很多都是金色的底,因為我之前有到唸到佛經,說有說金沙布地,那這個跟佛經的典故有關係嗎?
袁──沒有關係。我剛有講說這跟太湖有關。我們畫家是視覺動物,視覺做引導,當時給我的影響是,太湖水面波光粼粼的光,而夏天的光是金色,所以顏色是用金色來表現。跟浮世繪、佛經沒有關係,主要是感知經驗,與視覺的感知經驗有關。
姍──視覺的感知經驗去創作的手法?
袁──對。譬如我一九九二年開始在金山地方住,這個地方冬天多霧潮濕,白色的景象就會比較多,所以我早期一九九二年搬來這邊,開始受到這邊環境的影響,作品會偏比較淡,比較白。現在氣候變遷比較沒那麼多水氣,但是這裡相對其他地方水氣還是比較多。
《袁氏皴譜:書名頁、序》,80.4x142.7cm,羅紋宣、水墨,2019
《類山水No.58》,六件一組,49.9x57cmx6p,總長149.7x171cm,彩墨宣紙,2018
墨的兩種呼吸方式
姍──另外我滿好奇《火墨》系列作品,可以跟我們談談你在創作的過程,怎麼樣想到用這個方式作為水墨畫表現?
袁──主要是2015年去北京的時候,去的第一天就霧霾紫爆警報,一下飛機就開始戴口罩。我是屬於比較敏感的體質,北京這個空氣的味道,還有氛圍對我影響很重,因為一落地就開始咳嗽咳不停。。那個時候空污實在是太鋪天蓋地了,沒辦法忽略它,已經形成國家級警報了,你就會正視這個問題。二十一世紀地球暖化,空氣污染造成氣候變遷,未來我們會常常遇到。我就開始關心這個。那時候是去交流活動,我們要做一些現地創作,本來要拿「類山水」去展覽。到那邊就改變,改做跟空氣有關的題材。在北京我就在思考怎麼去因應這個空氣議題,又不能脫離自己是山水畫家,以山水畫這種傳統文化脈絡去對應這種新的山水狀態,所以想到用宣紙。水墨用的墨條來自於燒木頭取炭灰,調膠做成墨條,加水就能畫。宣紙同樣是來自於樹、樹皮,經過水的過程,泡軟打漿。它的原料跟墨條是一樣的,都來自於樹,一個是經過火取炭、一個經過水調製、打漿。既然原料一樣,我就把它還原。把它燒了再還原回到炭的狀態。宣紙作為山水畫常用的媒材,我將宣紙改為畫火墨的炭灰來源,以取代水墨的墨條進行作畫,這可以說是一種觀念藝術,是從物質的文化屬性來進行傳統工法的解構。它呼應著山水畫裡的物性脈絡,在對比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差異,也同時提出文化物質工法的新舊辯證關係。同時,在對應時代流轉後的氣候變遷現象時,也是透過同樣材質的差異表現,清晰地展現這個古今變遷現象。我在想古畫中的空氣總是美好的,而今空污的差異性,就要找古畫裡足以代表空氣美好、滋潤水墨的山水圖像作為臨摹對比的對象,用「火墨」去臨摹水墨作品,藉此強調氣候變遷與時代變異。 所以用宣紙的炭灰直接對臨古畫,這是完全以「火墨」的燥性所代表的空污霧霾對比古典水墨山水畫裡氤韻華滋的潤墨。過程中不加任何水,也不加膠,不用膠去固定它,讓它在宣紙上自由地飄動,象徵霧霾微粒在空氣中飄動的樣子。
姍──原始的狀態?
袁──宣紙燒出的炭灰,畫在宣紙上,它們是同材質、同質性的東西用手去畫。畫完黏著在上面,要掉就掉。在二〇一七年「墨的兩種呼吸方式」個展,我主要就是提出墨的兩種方式:水墨與火墨進行所謂墨性語言的物性辯證,它是材質性的辯證,同時也是材質背後所代表的古今美學觀點的對辯。當代的山水畫美學不見得要完全依循傳統美學,有時候需要從傳統的反面去帶出古今差異之處。過往傳統水墨背後的美學語言都要潤墨,所謂渾厚華滋、墨瀋淋漓,都是要表現水氣很美好的那種墨韻感覺。但是我用「火墨」,它反而在強調燥墨,燥墨要對應的是氣候乾燥、野火災難、在空中飄散的pm2.5空污微粒,而不是潤墨,這是古今氣候變異下所產生的美學語言變異。把傳統沒有表現過的反面的東西顯現出來,古典山水畫總是要追求或表現美好的桃花源、理想世界這樣的概念,但在二十一世紀空污氣候的當代,這樣的美好理想世界,因為空氣的問題,或許反而成為對當世一種再也回不去的嘲諷。因為氣候變異、暖化空污所造成的影響,美好理想的空氣會慢慢消失。用燥墨、火墨去對應潤墨其實也在講古今自然的變異。二十一世紀地球氣候變化太大,「火墨」發生在現在,是反映了如今真實的世界樣貌。
姍──像現在是疫情的年代,這個議題會放進你的創作裡嗎?
袁──創作前提是我要有感覺,目前還沒有感到這個議題需要我來做。。
姍──我感覺創作環境對你很重要。
袁──我所經歷的感知會去反映在創作裡。山水畫從古代就開始談「真山水」,但什麼是真山水?每一個時代都有談什麼是真。有人認為的「真」是表現親眼所見,對我而言,「真」不只是肉眼的,也是身體感知的,更是精神上所感受的。創作者面對自身真實所經歷的,不為了符合傳統美學而去逃避自身真實的感受,即使與他人或古典美學說的是不一樣的話,也勇敢地真誠表達。
姍──我滿好奇你探討水墨真實的本質是什麼東西,就像火墨這樣子。像它們本來都是同樣的東西,它們之所以不同,在於它們介質的改變,而讓它們成為一件作品,是對於本質探索的問題或見解?
袁──《火墨》探討的是我們如何透過重新看待墨的物性本質,去實質地將這些文化物質作為我們創作上表達的工具,而不是被傳統的使用方法所限制,這是跳過歷史眾相的文化侷限,回到創作自身語言所需去重新使用材質工具,並且重新定義、詮釋,賦予舊的物質新的觀點與美學語言。水墨沒有所謂真實的本質,因為我認為創作該有的自由在於不役於物,「物」不管是物質的或者性質的,都不應該被限制在單一的文化邏輯中。所以我喜歡拆解過往已被定型的概念。《火墨》拆解的是墨的物性,《類山水》拆解的是「皴」的形意語言,我的另一個系列《時間之漬》同樣也是在拆解,拆解的是傳統水墨常使用的「積墨法」,把原來「積墨法」的積墨而厚重,變成積墨而輕透。這是在材質與技法之間探討新的關係,是有關時間的觀點,而不只是在談筆墨美學而已。過去積墨法主要是在談筆墨造型美感,而我則運用現代攝影製作成影像,將積墨法裡的時間特性拉出來彰顯。
《墨的兩種呼吸方式》個展裝置一景,2014
《火墨.許道寧秋山漁艇圖》,畫作49x210cm供桌W100xH80xD30cm,宣紙炭灰於宣紙、灼宣紙卷裝置於白色供桌上, 2017
舞山水
袁──二〇〇七年間,不是只有《類山水》,我還有一個系列叫《舞山水」。《舞山水》是沒有草圖,將紙鋪在地上,不是桌上。用整個身體跳躍去運動,是一種情緒的直接反應。那個舞山水的畫是很大張,只用線條。那個線條就是當下的直覺性,身體表達內在的情緒狀態,透過手指去表達出來,大部分都是用紅色的硃砂和硃膘顏色畫線條,我當時尚未接觸西方的「陰性書寫」理論,但直覺就是要用類似經血的顏色來畫。那種畫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就是它更直覺性。所以那個畫很多,但最後只剩下七張拿出來展,其他都不行。
奈──所以創作是自我療癒,會想到給別人看到,這個是很大的不同?
袁──在畫的時候只關注自己,並沒有想給別人看,那就是一種抒發,畫完了,有人來看,覺得不錯,願意幫忙展出,就展示出來。不過,我也會在不同系列裡去探討水墨畫的一些歷史問題,並且將這些思考混合在感性之中,用自己的想法表述出來。
《舞山水之流形生發系列No.1-7》裝置現場,232x50cmx7件,淨皮宣卷軸、硃砂、泥金、礦物顏料, 2010
《時間之漬 No.6》,134x66cm,蟬翼宣彩墨,2007-2017
袁慧莉簡介
袁慧莉1963年出生於台北,曾以袁澍、袁漱別名發表作品。1987年畢業於第一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水墨組,2005年取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碩士,2016年獲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士學位。創作結合傳統水墨歷史思考與當代多元新觀念而別出蹊徑為特色,被視為台灣戰後現代水墨發展史第三代中極具代表性的當代水墨畫家之一。現為耿畫廊經紀藝術家、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