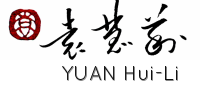平淡的可能與不可能-----一個藝術家的探問
袁慧莉 寫於201104
平淡是從老莊開始的哲學,漸漸成為中國繪畫(尤其是文人畫)、音樂、文學(尤其是詩)的美學與品藻的一個重要命題。
淡,按其字面看是濃的對比,《說文解字》指其本義為「薄味」,又因其無五味所以從水,日常的使用大概都以無味為主要的解釋,所以可以引申為清靜平和的狀態。但事實上,在中國某些日常的用語中,淡卻又不是這麼地清靜平和的意思,它反而是相反的另一個用意,例如:具有故意作弄的意思,像是「扯了一個『淡』」[1]。同一個字,日常使用的反差竟如此大。更何況當這個字被使用在美學上又加上了一個「平」字,並且它的意涵「在中國文化之中不斷更新,從未受到局限」[2],於是平淡就不再如其字面那麼地簡單平常。
我們可能掌握平淡之意麼?名稱與意義的分歧與符號在時空中所產生的任意性又使得可能與不可能間可掌握的界限令人困惑。
平淡究竟是什麼?是視覺的上的淡墨輕煙,渺渺氣韻?還是意境上的空靈虛無,雲淡風輕?是一種幾無的狀態,還是萬物的映照?是一種超脫遠眺或是靜觀內視?平淡就是慢與靜嗎?
平淡如何顯現?在具象中?在抽象裡?在材料中?在技法裡?在雲淡風輕的生活裡?或在生命的各種映照中?淡淡墨跡就是嗎?濃濃金碧不可能嗎?是在形式上就可以判定?或是必須從內容中加以考察?
這個古老的議題與美學品題在歷史上所成就的厚度與內涵在當代還有可能嗎?或是當代追求的另一種看似平淡的平淡已然有著演化上的異質?
思維平淡到底是什麼,這個乍看簡單實則不然的一個詞,看似已然理解了某個定義卻又發覺其定義的邊界實際上又是極度模糊的,其能指與所指之間有著一種擺盪狀態。所以,我試圖了解平淡並透過這個了解的過程回看自己的作品,是否具有平淡的可能。但我不是在作語言分析,而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探求,以免落入自以為是的論斷,雖然這個探求也許可能指向一個總是在變化的事實。
自然映照
淡既然從老莊開始提出,不如就來看看老莊的想法。
在一開始,原來只有「淡」的提出而沒有加上「平」這個字,老子在《道德經》裡提出「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3]的一種描述「道」的狀態。這裡,老子已經將「淡」定調為無味,我們還有什麼好再深索「淡」還有其他的意思呢?事實不然,因為老子只指出了淡的無味這第一義(事實上,道德經裡也只有提到一次的淡),他提出的是一個解釋,就是「道」等於「淡」等於無味。然而莊子在其論著中不斷地捻出這個「淡」字的時候,就不一定是這麼簡單的意思,有人還將它延伸出了第二義。
《莊子》〈應帝王〉篇裡提出:「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有的說法將這裡的「淡」以清靜恬淡之義解釋[4],這是沒有離開老子本義的解釋,但是如果按晉郭象(252-312)對《莊子》的注的解釋就不是這樣了,而是:「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5]任性不是胡亂作為,而是指順應本性,也是一種順其自然的映照狀態,無所飾指的是不刻意矯造、是純樸順性。倒是「漠」在郭象注為「漠然靜於性而止」,比較近於清靜的意思。對郭象而言,「淡」是任性,既非指味也非指顏色更非單指清靜,這裡可以看到郭象對莊子之「淡」是一種「盡物之性」的看法,而一般論者認為,郭象的注是較接近莊子的本意。為什麼呢?因為在《莊子》的外篇裡有以水來比喻這個「淡」的狀態,那不僅是味道的比喻而且是明鏡的比喻,這就使得郭象的順性映照的解釋比較呼應。
「水之性,不雜則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6](刻意)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7](天道)
《莊子》不僅以水或地這兩個自然物來說明,並且明確地提出了「平」這個字,對莊子而言,水與「淡」是質地相同的,而水的平靜狀態更具體地顯現了「淡」不僅是無味,還因平而如明燭般可照鬚眉的功能,所以虛靜、恬淡、寂漠、無為都可以顯示這種明鏡般的狀態。既然是平的,那麼,不僅是水可平,天地之平也可以涵括進來。
「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 [8](刻意)
這兩篇以水之「平」、地之「平」來喻「道」與「淡」,就將「平」與「淡」做了一個結合,也以「平」作為「淡」的更進一步具象化的解釋,「平」乃為水之平,水平則靜,靜則能明,「平」不僅能使水面如鏡,更因其「平」而帶出了一種平衡與道德質地。
所以,後來「平淡」結合成為一個詞,其本意是要指向一個虛靜而明的狀態,這個虛靜而明的狀態像一面鏡子,照見各種萬物之本然,使得萬物之本然得以自然呈現,是一種順其自然的狀態,毫無勉強造作,徐復觀也說:「淡由玄出,淡是由有限以通向無限的連結點。順乎萬物自然之性,而不加以人工矯飾之力,此之謂淡。」[9]如何能夠透過有限以通向無限?這句話的重點在於後面的順物之性與不刻意矯飾的態度,從郭象到徐復觀都對莊子的「淡」之意如此解讀。
所以「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應帝王)是以淡為游心天地的方法,所以當心處於虛靜無為如水般的明鏡及平中準的狀態,這個照見就使萬物得以各按其位自然化生出各種可能。物與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映照狀態,物之虛靜本然乃是莊子所謂自然,當主體虛靜之心與客體之物合溟,便進入了這個自然,當進入了這個自然,便是與物合一的狀態(物化),就好像平靜如鏡的湖面照映著周圍的山色與天光雲影,而當人的內心也像明鏡一般地皎潔,當然可以游心於自然,也可以說自己(主體)已與自然(客體)合一了。
這可能就是《莊子》在平淡中給出的「淡」的第二義,經由郭象點出,就是在映照中超越了無味而走向有著更豐富多元的無盡的可能。而平淡也與水與鏡子產生了連結,亦即水的無固定性與鏡子的映照特質也與平淡有了意符上的關連。
平淡有著自由且拒絕刻意的特質,所以它強調著自然而然,順其自然,是一種在自然之中產生的狀態,「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順性而為,不勉強造作,可以說平淡就是一種自然映照順性而為,平淡體現的是一種當下。當然,為了達到明鏡般的順性映照,必須是處於虛靜的精神狀態,所以「合氣于漠」也是心能夠游于「淡」的必要條件。
生活必需處於精神的閒靜安適,才能使心有空餘之處來領略自性與天地之間互相映照的透明流動。在1992年筆者從居住了將近三十年的台北鬧市與煩囂的生活中脫離,至2000年絕塵離世獨居的山居生活中,的確領會了這樣的境界,所謂「游心于淡,合氣于漠。」就是日常生活的狀態,因為當時筆者生活的環境就是一個可以遼看廣大海洋與天空的山頭,在那山頭的靜坐之中俯看著北海岸裡錯錯落落的小山石,周遭是雲煙供養空霧繚繞的氣候環境,陶潛的詩「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就是生活中的日常之景,蒼穹無盡,歲月不在曆日中度過而是在日月星辰與寧靜的細品中漸次累積成一種影像,在寧靜平和的生活中,才終於深刻體會蘇東坡「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的意境,當時的自己的確是得以將塵濁之氣澱清,使自己的本性漸漸顯現出來,而那幾年胸中滿溢了生活所給予的自然印象,靜謐的氛圍充滿了身體的每一吋細胞,當提起畫筆,筆下的圖像自然投射出這樣的感受與氣質。半年雲霧繚繞的山頭以及遼闊的山海視野使我畫面的構圖自然化生成塊狀山水的格局,山石的距離拉開了,留下大量的空,因為我所吸納的日常影像就是這樣的大塊山水。而我將多餘的雜質去除,只留下精煉的線條與色彩,淡淡的筆墨所呈現的山水不再是模擬的傳統山水或是自然的模仿,而是經過重新洗練過的精華,簡與淡是樸素生活的自然而然的映照,「天地無言而無盡言」是當時寫下的感言詩句,自己浸潤於這樣的生活,繪出2000年首次個展「居山飲壑」的一批布畫作品,當時的畫冊自述裡記錄了我的真實體會:「在單純中才能細細品嚼生命的美好,感覺自己心靈的脈動。…在簡單中才能領略豐美,…唯有單純寧靜可以沉澱人的心靈得到一種澄明通透,由此心如明鏡,照見五蘊,直抵萬物之根本。」[10]
現在回看,原來自己早已領略過「平淡」的自然滋味,也以作品反映了這一種生活氣息,那八年的平淡與寧靜,大概是我有生以來最為豐美的日子了,在那段日子裡,我開始認識了自己,不但與自然對話也與自己對話,發覺自己的本性是如此地喜愛寧靜,在極度平凡的生活中,「我感到平淡無奇的生活中有種芳香,這香味極淡卻悠遠,是一種生命的底蘊。而我願歌詠這底蘊、這芳香、這平凡。」[11]
不過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就是一種「平淡」的意境,而是所有的細胞都在吸納並浸潤著,那是對平淡的直覺領受,如同呼吸般地自然,如果我當時刻意理解這平淡的話,那麼,我可能就無法真正的享受著平淡,這真實的平淡就不再可能了,而只是一種追求罷了。當時自己的創作狀態是將身心所吸納的生活氣息轉化為筆墨,有時畫作的完成是在一種自然溢出的狀態下一氣呵成,好像那些圖像已在胸中蘊釀成熟,呼之而出,每一筆的出現都是那麼流暢自然,無一勉強,行筆的當下,有著一股氣促使著我行動,畫作通常是放置在地上,而身體在這畫作上行動,筆順著這股身體的氣游走,執行著將胸中的圖像完成的任務,古人說:「下筆如有神」大約可以形容這樣的創作狀態,我認為,這不是神明降臨,而是在山林間居住的那幾年所充實的內在積蓄所致,身為藝術家,這內心的靈敏感受最終透過指尖自然地流洩出來。
二元合中
于蓮(François JULLIEN,1951)在《淡之頌》裡開宗明義認為平淡是:「拒絕有特點、不引人注意且含蓄」。[12]又說:「平淡的特點,是它無法被任何一種特殊的決定因素固定下來,因此能夠變化無窮。」[13]這兩句話加起來有一個邏輯就是:沒有特點的特點就是平淡的特點。
這個邏輯和金剛經裡說:「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一樣,也和夏可君常說的:「什麼都可以,什麼都不可以。」很像,都同存並置了接受(肯定)與拒絕(否定)的二元邏輯。徐復觀說:「由玄所出的淡,應當包羅自然中一切的形相,而並非侷限於某一形相。」
所以其定義是浮動的,一但落定就不是了,這就是一種在兩極(是與不是)之中擺盪的狀態,一面肯定同時也予以否定,就是不能具體地肯定與否定,所以「平淡」存在著一種兩極對比並置互補的狀態,「平淡」也必須在兩極對比中呈顯,如同老子說:「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在否定言說中卻又以道德經從各個角度在說明道與德之意,這就好像禪宗不立文字卻又有六祖壇經一樣,在拒絕(否定)與接受(肯定)中,有著互顯的激盪,而真相有可能在這個正反激盪中顯現,因此形成非二元對立而是二元並置。所以老子說「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多﹐多則惑。」(道德經,二十二章)與莊子說「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莊子˙天運第十四)都在強調兩極對比互補與差異並存且互相運作的重要,這是所有變化的根本,也是保持運行和維持活力的重點。就像「無」是相對於「有」而存在的,所以像「當其無,有器之用」(老子,十一章)「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老子,二章)所有萬物的產生都是透過相反的兩種極端特質加以互相對襯而相成,這不僅突顯「道」具有包含萬物的本質,也說明「淡」作為「道」之出口也體現這樣的並置與矛盾的組合,代表著「淡」沒有固定定義同時又包含各種定義,既是自然的所有映照,當然也就包含著正反兩極的對比並存。也就是說,平淡是在相反相成之中去除掉絕對性與封閉性,不在辯證對立中。
「平淡」正是有著這個開放性的特點,所以,「平淡」應該拒絕落定在絕對的單一虛無枯澹乏少的解釋與追求上,因為一旦落定便意謂著消解對比並存的差異性,看似淡實則是一個極端狀態的顯現,同時就封閉了淡的變化的可能性,反而「退化為平凡和平庸的狀態」[14]而不再平淡;這就不難理解蘇東坡要特別強調:「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又說:「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矣。」(〈評韓柳詩〉)就是要點出一眛的追求淡泊蕭索有可能反而枯而不實,而必須同時外邊枯澹和中間實美並存。反之,也不能落定在過於實美而沒有枯澹的富麗中,那形成俗艷或沒有餘地毫無想像空間的狀態。
所以,在這種具有兩極並置對比互補的哲學觀點之下的中國山水畫,也就沒有走向絕對的抽象和絕對的具象這兩個極端的畫風,而是具象與抽象並存於山水的造型與筆墨中。具象言說描繪得太清楚而失去餘地與想像空間;抽象則餘地太多距離太遠常落入難以理解難以產生共鳴與交流的基礎,有時還必須透過解說,這產生了間接的鴻溝與拒絕直接交流共感的狀態。有趣的是,平淡的一個重要的質地是強調直觀(自然映照),如果在當下還要透過解說才能理解就不可能是平淡,余蓮說:「真正的直觀便是,通過感覺上超越象與實之間的界限而臻至的。」(2006:頁114)又說:「平淡不帶我們去尋找另一個意義,不去探求一個隱藏的秘密,將我們從意義辨別的特性裡釋放出來。…沒有理智對抗感覺,也沒有偏重本體而輕視現象。」(2006:頁116)
平淡拒絕太直接也拒絕太間接,它在對比互補中形成平衡與和諧,因此它也體現了具融合狀態的「中」的特質。余蓮說:「平淡那捉摸不定的性格,便從這種矛盾當中透露出來,因為只有在可感的事物之盡頭與不可見的事物之門檻上,平淡才出現。」(2006:頁77)既然平淡在矛盾互補中建立其變化性,也就建立其層次感,平淡因此不可能是單一的或單向的,它既是一種映照狀態,就是有著兩邊,而這兩邊是一正一負,一陰一陽,一上一下,它不再僅指向出口,而是一種映照,是雙向的,有著在對比中進出而流動的狀態。既然這映照不再單一,那麼所有的味道都可以體現出「自然」之味,這裡不再是無味,而是一切,所以,就像蘇東坡從佛語:「人食五味,知其甘苦各皆是。」中所領悟的,而在他〈送參寥〉詩中的呼應:「鹹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就是要點明,即便是鹹或酸這些味道中都有其雋永的滋味。關鍵就在超越,不執著於任何的特殊味道,也不被束縛,「中」是在既包容差異裡又超越了差異。平淡在超越中顯現。
雋永與超越
平淡在包容差異之中可能顯現其超越性,但我一直好奇著,到底平淡的超越性可不可能藉由否定而達到?如同林壽宇藉由去除筆墨否定筆墨來達到其絕對性的白色之平淡世界,也就是說,為了要達到平淡之途,筆墨的剔除是一個必要途徑?林壽宇以一種抽象的絕對姿態來表現對文人畫的筆墨質疑,在看似平淡的畫面裡,是否真的有著平淡?如果有,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平淡?是視覺的平淡還是意涵上的平淡?可以簡單地將視覺的平淡效果等同於內容的想當然耳嗎?立足在否定筆墨上的「極少」有可能就是平淡?還是推向了極致貧化邊緣的餘跡是平淡?如此強烈的絕對強調與手勢控制有可能是一種平淡之姿?當平淡要以控制走向絕對的否定時,是否同時也可能消解了平淡自身?(一種刻意的雕飾痕跡反而在其中顯現。)當他的絕對性控制還遺留著「精微的筆墨觸及」[15]的文人痕跡,這去除筆墨的不可能性也同步呈顯,從林壽宇的白色系列作品中,這種形式與內容的曖昧難明與自我矛盾性似乎在西方的絕對抽象理論裡並沒有也不可能被閱讀出來,只有透過對於中國哲思的「平淡」意涵的考察脈絡裡可以看到。無怪乎最後他會走向對繪畫的根本性質疑與否定(在1984年宣示「繪畫已死」,從此不再繪畫)。正當其作品觸及到平淡的矛盾性與耐人尋味的邊緣時,他卻選擇放棄繪畫,他的放棄是否正表明了他的立場:一個絕對激烈的與筆墨切割的態度,他不要模稜兩可,他要的是絕對化,是精準的視覺計算,沒有商量餘地的絕對去除筆墨的聯想,從幾無走向絕無。
平淡如果只是單一的一種絕對姿態,就不可能是映照萬物的明鏡般的天地之水,而只是一杯水而已,一杯清清楚楚僅能止渴的水,而不是有著無限可能的雋永。它映照萬物,所以既不消除任何特殊的味道,但也不迷戀。它讓所有的味道自己顯現其味道,這些味道本身的內在本質自然會有屬於自己的雋永。更進一步說,平淡也可以容納不同味道的互補,使原本對立相反的味道產生相輔相成的更加雋永的滋味,透過不同味道的結合產生更豐富多樣的變化,在融合中平衡其味,中和各自差異(而不是消滅差異),使得原本的味道透過融和而達到另一個超越的境界。平淡顯現自然的本質:在對立矛盾中融合,並且達到平衡,而這個平衡因其具有豐富內涵而得以雋永。所以最高明的平淡是:「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于淡泊」[16],也就是在不平淡中達到平淡。這不再是簡單的映照,而是像余蓮形容的淡是一種側照,含蓄的斜領,非直接的,而是帶有轉折的。這是對於落實在創作上,就有著對於超越的要求,超越太過簡化的直接的抒發,超越複雜的多而凝煉成少,因此在看似少的表面裡存在著豐富的內涵,「簡而愈備,淡而愈濃」[17]。所以余蓮認為,「在繪畫和其他的領域裡,平淡乃要求轉化,這也是平淡的價值。」(2006:頁127)在平淡的表面之下必須有著身體與自然之間的迴轉,這個迴轉形成一種深沉的回音,是一種由近而遠的回響,這個回響又從遠方轉折回來喚醒我們,是在平凡中的一種超遠醇厚,而非一無所有只剩遺跡的形式殘留,在看似平凡中卻有著醇厚的轉折,在簡淡中有著豐富的轉化。
余蓮所謂在繪畫中「平淡乃要求轉化」,這是他觀察到山水畫家筆墨的培養訓練最終要達到的境界,為什麼中國山水畫的筆墨漸次形成具有著某些規律與技法特色與法則,而不選擇直接的自動性技法,這不是更有順性而為的映照可能?即便最不按牌理的徐渭其瘋狂的風格中也有著精煉的筆法,懷素狂草的自由奔放卻還有著懸崖勒馬的筆法精準度,在自由與控制的兩極中表現了令人喝采的平衡力道。余蓮指出:「只有當『法我相忘』,當藝術家超越了法我之間對峙的關係時,他才能達到『平淡天然』」(2006:頁127)在這裡,余蓮將「平淡」的可能性與「超越」做了連結,在於其中有一個法的約束,這個超越才能成立,這種平淡帶出了時間的特性,超越需要時間的學習與轉化。其實,正是中國筆墨的法則的存在凸顯了超越的可貴,平淡不經過轉折的過程就不會顯出一種在限制中所臻至的「超越性」境界,這個「超越性」不可能在去除筆墨與否定筆墨法則甚或毫無懷疑地接受筆墨法則之中存在,而是在被約束中超越約束才能顯現,超越法我對峙的關係是將法化為我用,才有可能平淡,而不是脫離這個法或被這個法所拘束。他認為在山水繪畫裡沒有技術超越就不可能有平淡,就這個角度看他是認為筆墨的法則的存在具有其意義,在這種超越中才能「不立刻滿足我們最淺薄的品味,而是呼喚我們的內在性更往深處潛入。」(2006:頁128)
中國繪畫筆墨的存在代表著它之為中國繪畫的特色所在,就像每一種技術都有其技術性的要求,如果太極拳消解了其內在的氣功技術與招式的力道,表現得像舞蹈,還能稱其為太極拳嗎?如果任何一門球技的球員不經過學習技術進而超越技術門檻,如何能夠成為佼佼者?每一個佼佼者都不斷地在前人的技術上墊高其難度,而這正是專家必須超越的高度,真正的高手是努力的學習其高難度的技術並且跨越這個高度,這才是真正精微的力量顯現之處,高明的藝術家能夠入法而超越法不被法所拘束並給予創造,採取的不是一開始的否定與逃避,而是有自覺的學習與接受,並且是持續不懈地日常的精進。繪畫技術或武術或其他技術都是他人留下的生命風景,學習這些正是讓自己從與他人的生命映照中獲取豐富的資源來厚實自我,每個人的天性有限,能夠有多少內在資源可供長久揮灑?如果沒有與其他生命一起產生映照關係,如何能夠得到共照的豐厚性。學習前人法則顯示的是容納他者生命的進入,而非排除在外,是一種虛己以待的映照,然後在包容之後轉化成具有個人面貌的創造,這種超越是一種內在修練的結果,但這是漫長與辛苦的自我鍛鍊過程,需要的是時間累積與日常磨練,更需要敏銳的自覺能力,在這一切講求速效的時代,有多少人能夠做到這種需要時間與耐力來達到轉化結果的平淡功夫呢?
西方的藝術是從否定中誕生新的藝術,在斷裂中產生新的意義,但,中國的山水畫則是在超越中誕生新的藝術,在接續中展現超越的力道,這使得新的意義得以與歷史舊的意義一同敲出不同回音的共鳴,其音不再單薄,即使輕微,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中國作為現僅存的最古老文化還能繼續存在的原因之一。平淡不就是具有一種長遠存在的時間性特質,一種永續不枯竭的狀態。平淡不否定也不接收的特質,使其保留了超越的餘地與彈性。全然否定代表沒有超越的必要,那是自立門戶,自定場域;全然接受代表沒有超越的彈性,那是照單全收,場域僵化。而平淡在否定與接受中保持超越性。
這個超越性使得平淡得以避開枯竭乏味的可能而達到雋永的深遠醇厚狀態?在余蓮《淡之頌》最後一章討論到超驗性的時候,他認為中國人以淡而無味的水來象徵一切萬物的根源是一種轉變,而這個「轉變的之外就在其內裡」,「淡而無味是將意識帶領到現實的根源,帶回到事物從它開始演化的那個中央,它是進深之道,也是淡漠之途。」(2006,頁139-140)也就是說平淡不能在刻意追求的情況下獲得,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整體內在呈現,且這個內在是在經過了調合的過程之後的一種轉化。
所以經過轉折的平淡是「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一種感悟之後化萬味于淡然的一種超越,既是對技法的超越,人情世俗的超越,也是對自我困頓生命的一種超越,這種對於水的比喻,是一種「反璞歸真」的境界。這裡有著在糾葛衝突之後的回歸本樸,就像蘇東坡在赤壁賦裡呈現了在被貶的困苦中展現的超越世情與通達境界。這一種與清風明月共享的當下平靜,是將關注的視線從生活的痛苦與艱難的近的凝視,轉變成望向天地遼闊與超脫的遠的凝視,這就是一種「遠山無皴」「遠海無波」「遠波無聲」[18]的意境,在遠的狀態中超離了各種塵世的紛擾,所以「心遠地自偏」,是一種自我超脫的狀態,這種超脫不是走向虛無走向否定,反而是在遠的距離之中得以有餘地安置內心,保持內在的平和,使得自我生命不被塵世耗盡,而能維持不止息的生命能量,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積極態度,是在關注萬物的修練中,以超脫達到無為的寧靜,回到平衡的生命狀態,使生命回到明鏡般的照見,達到單純而醇厚的平淡。
「遠」的提出在於一種超脫的態度,超脫不是離開,而是擁抱更廣大的境界,所以中國的詩境喜歡強調「俯仰放懷抱,宇宙何其寬」[19],「俯仰心境寬」,俯仰之間就是自己的心所居處的位置,望向遠處其實才能打開餘地回看並觀照自我的內在。
關注自我
既遠而返,望向自然大塊,也不能不回看自身的存在真實,平淡不能忘記身體當然就不能不包含這個主體的情感與這個主體所存在的遭遇。
莊子所提出的「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原本這句話是應帝王篇裡無名子回答天根問有關治天下的治理技術時給予的答案。這不僅牽涉到莊子的自然觀,同時也顯示了對政治管理的觀點。其實就是希望統治者將這個治理權還給人民,使人民擁有自我管理的自主權,讓一切自然按其本性生成,不必刻意管理,讓一切物性自然映照其自身的狀態,盡物之性,就是一種將關注轉向自我並且順著本性讓一切內在自然地映照。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主體解釋學》裡思考到自身以及他所處的時代困境時,從希臘古典文籍裡尋找有關主體的詮釋時,他特別就自我關注的問題進行歷史考察,從這裡,希望找到人之存在的重心與必須關注的對象,那就是關注自己。他說:「轉向自身的概念。完整的主體必須轉向他自己並關注他自己。」[20]這當然是指在西方揚棄了上帝的這個主體之後,人類從原來的客體轉向,關注到自身可以成為完整的主體的這個歷史脈絡而產生的尋找之路。福柯認為人應該透過關注自我達到自我救贖的,而非透過上帝的賜予,或者期待制度。
東方則略有不同,沒有上帝這個天父作為人類精神的統治者,但是封建制度裡的統治者成為天賦帝權家天下的父,階級觀念不只在政治制度上,也存在於家庭中,在這階級傳統裡存在的女人,多半是附屬於丈夫的客體,女人是一個忘記身體的客體,她要關注的是她的丈夫以及孩子,就像被統治的子民服務於其主一樣,所以,女人如果要成為主體,就必須看到自己並且關注自我。
即便是男人,在中華民族的階級政治歷史中,也很難容納太多的主體,因為權力主體只能有一個,那就是統治者,所以,當某些有識之士體會到自己的存在價值是一個獨立的主體,而不該是由一個主宰者決定的客體時,或者是當個體在這個統治主體之下無法施展抱負不被重用時,他們多半會選擇遠離這個政治主體的統治而進入鄉野或山林,成為隱居者並寄情於山水之中,在一種遺世獨立的生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並且投注寄託自己到山水之中。
不像西方的宗教求諸上帝,在東方的佛教或禪宗裡,強調人人自性中皆有佛性,不必外求。連孟子也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1] 對於自性自心的看重是東方哲學與宗教的特色。
「游心於淡」強調的是心游化於淡的狀態,沒有了這個心也就沒有游於淡的主體,也就沒有映照之所,所以這句原來做為政治治理術就轉化為個人的自治技術。這種轉化尤其在山水畫論中可見,最明顯的就是將老莊思想融入山水畫論的宗炳,他說:「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22]人的內心藏著山水,山水裡也有靈,所以中國的山水畫是一個擬人化了的藝術[23]。山水不再只是山水,而可以是自我所投注的場域,是一個寄託之所,也是寄情之所。山水畫既是一個靈魂寄託之處,也是內在透過山川的映照。所以,從「仁者樂山,智者樂水」[24]開始到「我見山川多嫵媚,料山川見我亦如是」、「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25]、「夫畫者從於心也」[26],中國畫如此看重畫者的主體自性作用於繪畫之中,在於一切外在之物如果沒有了這個主體的映照,只是一種單向的作用並無法達到「物我合一」的雙向交流,那麼其精神境界必然缺少了一種來自生命的厚度與變化的可能,試想一個忠實反映的自然圖像只是一個圖象,如果沒有了主體的身體感知使之轉化交流運動出具有生命感的內涵,那種直接的圖像摹寫只是死物而已。沒有情感的平淡映照只是一種死寂,沒有生命力的平淡,徒留表面遺跡,麻木不仁,根本與平淡無涉。
平淡離不開身體更離不開生命的感情活動。如果是這樣,對於大自然顏色的感動卻要被水墨為上的觀點排除壓抑,這不是很不自然嗎?中國畫論史裡對色彩的排斥一直是有著相當份量的,其中要數董其昌的南北分宗論的提出所造成的影響最鉅。其實,就算董其昌沒有明確地貶抑著色山水,但他所強調的「尊南貶北」就將他歸為北宗的重彩山水直接與平淡天真分隔開來。
徐復觀在其討論到「淡」的觀點時,提出他對於董其昌所提倡的重南宗之平淡的批評,他認為董此說為害之大,使後來山水畫家將平淡理解為一種「一超直入」「墨戲」的「浮薄敷淺」賣弄筆墨趣味之途,遠離了老莊的本意也遠離了真正的人生,並認為這是「後來以南宗自命的人,多限於形式主義,而不能自拔的真正原因」[27]。徐點出了平淡的意涵在歷史裡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個轉折將老莊對于淡的原始平衡意涵轉向了一個偏頗拒斥的狀態,也就是過度的看重水墨的平淡天真反而使得中國畫的多樣性被侷限於此形式之外,徐復觀認為:「排斥自然中的某種形相,而局限於自然中的某種形相,這即是一種陷溺,即不能稱之為淡。同時,涵融自然之心,也會轉向社會的群體生命,涵融社會群體生命的悲歡哀樂,以將其融入於自然之中,表現於筆墨之上。」[28]他的觀點也是與余蓮一樣比較不設限地看待「淡」的範圍,他認為「淡」的涵蓋面不應侷限於南宗水墨一系,也不應侷限於柔弱的氣質一方,不應只耽溺於超脫世情之外,也應表現生命的悲歡哀樂,從這點來看,他是反對那種尊貶的二分法的,而有沒有「淡」的衡量是在於是否有「人為刻飾之跡」。不過,什麼是「人為刻飾之跡」?工筆山水或用色濃重的金碧山水是否可以被一概歸為這個範圍?
如果把工筆或金碧山水全然因其用筆較不自由隨意而拒斥在平淡之外,是否就輕易地犯了與董其昌一樣的問題,在太粗造的二分法中反扭曲了平淡的真意?如果「淡」拒斥了用色濃重的金碧山水,那麼天地之間自然的五彩的存在難道不該被映照?「董氏從筆墨技巧上去領會淡,也只是從筆墨技巧中的一家一曲去加以領會,這便與淡的真正意味,相去甚遠了。」[29]在董其昌尊南抑北的策略裡,尊水墨抑金碧是其背後的意識,平淡天真從此與水墨畫上等號,使得金碧山水的表現可能性與位置從此愈形艱難,,將老莊的平淡之意走窄了,也使中國山水畫的世界愈來愈狹窄,好像只剩下水墨可以與「淡」當鄰居了。事實上元趙孟頫、明陳洪綬所作一類的金碧、工筆將重色一派的畫風推向高古典雅,「發簡古於纖穠,寄淡泊于至味」,絕去俗艷之氣而表現出色彩「淡」靜的氣質,就是最好的例證。
真正的藝術家關注自我對外在一切的感應,不論是水墨或金碧,都只是技巧的不同而已,顏色有無與境界高下無關,對於將金碧摒除在平淡之外是一種以語言符號將平淡同一化的選擇,這是一種我高彼低的權力慾望作用下的企圖,也是文人畫藉以顯示其有別於院畫的一種策略。
生命的苦樂安靜或激昂如同萬物之色,自然地存在著,如果,畫者為了一眛符合超脫的平淡而不斷地壓抑自己內在自然發生的激昂情感與對色彩的感受,這就是一種「人為刻飾之跡」,刻意忘掉自己存在的身體所呈現的自然情緒,就是眛於自身的真實本性,最終有可能因為太過於克制而導致身體真實感的消失。
回到關注自我與身體自性有關的映照,就是從遠離世情的遠的凝視所可能漸次走向極端而導致虛無迷失之中警醒,回到自身的關照,順性而為,依據當下的內在生命感受表達他們的真實情感,讓生命的本然自然地映現,既不思考平淡也不刻意平淡,是回到身體存在的事實,回到自我的凝視,也就是在自我審視的自覺中,反省來自自身生存的必要而非外來或對誰負責,思維如何超越法則與制度對於介入個人生命所產生的影響,在這身體既存於世無法脫離的外在共照中,如何能夠建立自己的風格與存在美學。就這個意義上,創作是一個反省之路,是一種自我審視的映照,也是將生命的風景轉化為筆下風景的一個行為,更是一種自我超越的方式。
非結語
名詞如果已經定下它的定義,就會在它的定義中死亡,董其昌對於的「淡」的偏頗標舉分宗,已在無數的追隨者身上得到蒼白的印證(雖然他自己的藝術不致於是如此的結果),或許真正的平淡只有在過程中才能顯現,因為它是變動不居的。
生命並非單一不變的,如果「平淡」是一種自然映照,我們就看到了它的豐富性;如果「平淡」是一種順性而為,我們就看到了它的變化性;如果「平淡」是一種雋永超越,我們就看到了它的餘韻;如果「平淡」沒有去掉身體,我們就看到了自然映照得以存在的條件。
平淡是無法追求的,一旦追求就不可能自然;平淡是不可能刻意的,不管其形式為何,一旦刻意就不可能順性;但平淡也不是毫無轉折的直接表現,如果沒有經過轉化就不可能有雋永的可能。
經過對一些文獻的探索,似乎對平淡的輪廓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但是,這些理解是否也同樣對未來敞開,面對一個無可避免的提問:「平淡在當代與未來的可能性是什麼?」的時候,我們果真能夠提出有效的答案嗎?
參考書目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1998。
莊子,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台北:華正書局,民74年。
于蓮(François JULLIEN)著,卓立譯,《淡之頌:論中國思想與美學》,台北:桂冠,2006。
夏可君著,《平淡的哲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
米歇爾˙福柯著,佘碧平譯,《主體解釋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傅抱石著,《中國繪畫理論》,台北:華正書局,民77年。
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出版,1998版。
俞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台北:華正書局,民73。
[1] 見《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淡之義第三條引〈儒林外史〉之例句。台北:正中書局,1998,頁848。
[2] 于蓮(François JULLIEN)著,卓立譯,《淡之頌:中國思想與美學》,2006。原序。
[3] 老子,《道德經》三十五章。
[4] 見《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淡之義第四條解。
[5] 莊子,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294。
[6] 同上,〈刻意第十五〉,頁544。
[7] 莊子,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天道第十三〉,台北:華正書局,民74年,頁457。
[8] 同上,〈刻意第十五〉,頁538。
[9] 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頁416。
[10] 當時以「袁澍」之名發表第一次個展「居山飲壑」,並發表第一本畫冊,以「澍」為名是為了表明生活在水與樹的環境中,此句見於2000年自行出版的畫冊後之自述。
[11] 《居山飲壑》畫冊,袁澍自述,2000年,頁27。
[12] 于蓮(François JULLIEN)著,卓立譯,《淡之頌:中國思想與美學》,2006。原序。
[13] 同上
[14] 夏可君,《平淡的哲學》,頁49-50。
[15] 見筆者「精微的筆墨觸及---近觀林壽宇白色系列的筆觸」一文。
[16] 蘇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
[17] 明李日華,《竹嬾論畫》,《中國畫論類編》,頁130。
[18] 原句出於宋郭熙《林泉高致》「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後筆者引申作一種遠的意境解,有部分句子題于2000年作品畫上,以體現曠遠的生命境界。
[19] 明歸子慕〈雜詩句〉。
[20] 米歇爾˙福柯著,佘碧平譯,《主體解釋學》, 2006,頁238。
[21] 孟子˙告子章句上,「放」為失掉之意。
[22] 宗炳,《畫山水序》,錄自俞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頁583。
[23] 徐復觀在其著《中國藝術精神》裡有對於中國文人畫此特質的說法。見頁361。
[24] 語出論語。
[25] 明唐志契〈繪事微言〉,錄自傅抱石著,《中國繪畫理論》,頁10。
[26] 明釋道濟〈畫語錄〉,錄自傅抱石著,《中國繪畫理論》,頁8。
[27] 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第十章裡有對董其昌的南北宗論之問題的詳析批判,本文不多贅述。頁464。
[28] 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頁463。
[29] 同上,頁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