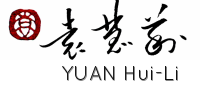|
物體無--在浪費的遺跡裡生產意義
展期:05/16/2018-07/.10/2018
地點:台中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策展人:華建強 華建强(策展論述)
本展邀請三位藝術家,分別是袁慧莉(1963-)、黃柏皓(1981-)與曾霆羽(1983-)。他們三人分別使用了不同的創作方法,卻同樣聚焦於探究東方媒材中的物性,以及利用材料的特質來對應於各自所面臨的世界,並依此呈現出濃厚的個人樣貌,進而凸顯自身或環境帶給他們身體上各種不同的感受。透過了這三種不同的創作方式,從材料的實驗過程到作品完成的階段,他們也在其中體現當下時空的感悟,或對生命生存的個人省思。 袁慧莉:毀壞過後的重生 袁慧莉的火墨作品使用了宣紙燃燒後的灰燼來作畫。這是將一個完整的物件摧毀,然後利用它的殘餘之物,使之再生,並且化作創作觀念上的必然之物。作品影射了大氣、環境與人為生存之間的矛盾。現今社會工業的殘汙飄散在空中,使得清澈的家園不再。此時宣紙作為空汙的代表,期間亦連結了自然樹木的人為製造所帶來對環境的破壞。而就在紙張被燒毀的過程中,不僅調侃了過往士人所遵循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從殘餘的灰燼所建構的山水之下,狠狠地諷刺了歷史畫作裡,對理想境地的投射與追尋。 撕貼的水墨是作為火墨成品的對照,但其實袁慧莉在對一幅完整的山石撕下之際,間接叛逆了傳統水墨在設計上所強調的可居、可遊觀點。此乃截取了山石後,再令每一個被撕下的缺塊成為各自的主體。透過了重新組構與拼貼之後,再去製造一處可不斷調整、變動的世界。如此一來,文人在紙上逸遊的思想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反映出現實世界中的變動、不安以及組構的環境。 黃柏皓:以多造無 黃柏皓作品看似單純與無物。其單純是因為透過筆刷將顏料層層堆砌,把整個平面空間填滿。畫面表現因此顯得均質,並呈現出一種類似真空的狀態。這是因為在他的創作過程之中,使用了繁複多次的操作,令畫面多到滿溢時產出均勻的質地。其均質與空無的關係因為上色次數的頻繁而產生出連結,正是在此連結之下,他規劃出來這單一色彩的世界,顯然就成為了材料滿布與空無關係中的相互矛盾與指涉的空間。 然而空無有著隱含無物的象徵語彙,而均質則是材料豐富的代表,並將既有的不均填滿。這兩者看似矛盾,卻又有所關聯。當均質趨於繁複與極致時,作品所呈現出來的一致效果,卻正是空無原來的基礎。因而利用「多」的手段來製造出「無」的效果,兩者本身就是一個極具矛盾與衝突的立面。但黃柏皓掌握了兩個看似對立的端點,讓「多」的添加趨近於「無」的狀態,儼然成為他抒發心性與創作的特殊方法。 曾霆羽:磨造的危機 曾霆羽製作了核廢料桶外型的墨條,利用危險廢棄物的形象與傳統用墨的結合,在古典文化的調性中置入了危機意識。廢料桶的內容物由核能改成了墨,頗有影射傳統書畫工具的一體兩面。透過墨的中介,轉化而成的文字既能造福人群,亦有可能是權威思想的毒瘤。而過往被視為心性鍛鍊的磨墨過程,在材料外觀的改變之下,更直接指涉了現代社會隨處潛伏的風險。透過一點一滴的消磨歷程,由固體溶解至流動的液態,滲透的方式隱微卻又瀰漫。並在不知不覺之中,風險擴展至整個社會。 此外,廢棄的建築石料所製成的台座,意指了人造環境的污染。不論是巨大建物的視覺感官迫害,又或者是利用消滅植被、強據自然的作法等等,其意義濃縮在這些殘缺的石料之中。進而,當核廢料桶與廢棄石料結合在一起時,這看似單純物性的結合,背後的意念卻不僅僅停留在物的拆解與重組的過程之中,事實上,它更彰顯出物件背後所隱含的多重意義的疊加。至此,作品反映了他關注於自身居住的環境問題,也擴展傳統歷史文化,在現代社會上是否仍然適用的拉鋸與反思。 物.體無:選擇除去的浪費 「物.體無」援引日本用語「勿體無(もったいない )」。其意義的來源則是從佛教中的用語「物體」的否定詞而來,意思是「當某件事物失去了它原來該有的樣貌,對於如此的狀態感到十分可惜與感嘆的心情」。然而現在則是表達出事情沒有辦法充分發揮其價值而造成了無謂的浪費之意。由此,本篇「物.體無」的概念所欲形塑的意象,則聚焦在創作者使用其創造的「物件」時所引發的一連串被普遍價值認定上的浪費之用而言。但對於作品製造者來說,這樣的「浪費」非但必須,往往也被視為必然的過程。尤其,此「浪費」又建構在他們刻意去除物體原有的型態、樣貌,或者是改變原本用途的意念之下而成立,它同時也具備了置換材料意義,以及拋棄物體原本使用的方法之包袱。 在袁慧莉的作品中,搞破壞與減法的過程具體而顯現。以火墨去除了宣紙原本的物質性樣貌,之後再以殘渣為材料來看,那些被普遍認定的浪費,就在於宣紙完形的去除而顯得可惜。此完形在被破壞的同時,也正是她火墨與水墨作品成形的轉捩時刻。尤其當這些破壞成為了創作上一個必然的手段時,「不完美的山水」,以及紙張的功能性「被浪費掉了的山水」,和宣紙看似「物非所用之山水」,都建構出了她依此浪費態勢而來的巨大價值。 黃柏皓利用筆觸的累積而刻意去除形體,試圖將指涉與敘事降到最低。還原物質本身所散發出來的魅力。其壓低材料的使用方法,在普遍認定的浪費價值中,只使用了材料的某個單一特質,也就是材料的本身。由於沒有具體形象去輔助材質的施展,觀者僅能從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物質性去探究原先規劃之目的。因此,一種普遍價值認定上的浪費油然而生。因為創作者只使用了純粹的筆刷當作步驟。這顯然與具象表現所追求的結構或空間的關係嚴然不同。尤其在他實踐以及執行意念的過程之中,那個不為所思的當下,正可與現今忙碌的社會為對照。於是關於浪費以及可惜用語之所以會被提出乃是其中的原因。 相較於另外兩位藝術家用繪畫的方式來操作,曾霆羽的裝置則是不透過毛筆為中介,以及沒有繪製圖像的過程。他以墨當材料,利用塑造以及置換造型、外觀的方法,試圖改變媒材長久以來被使用與觀看的慣性,將機械裝置當作人的手臂,成為另一種非關製造者自身勞動的動力。並以機器代勞,扭轉磨墨的過程中被一再強調的個人心智之磨練。在規律的機械性動作中,創作者設計與組裝器物,再透過那些被組織好的物件進行如常規般的物質性運動,因而機械取代修練的程序,並且明示了現代化的社會,勞動的可取代性。此外,在過往傳統書畫的表現裡,磨墨這件事,往往被視為作品製造過程中的其中一個步驟,此動作是中繼而並非終點。創作者製造作品的意識往往也不會僅止於此。正因為在磨墨之後,尚須搭配紙張、毛筆等用具,才能夠沾墨繪製圖像。所以,曾霆羽的磨墨裝置,其普遍觀點所指的浪費,就在於它只磨墨而不施作,並且沒有一般在認知上,作品產出的功能,因為磨墨這過程的裝置本身,就是一件完成的成品。 改變與再造:新意義的賦予 三位創作者在歷程中,同樣選擇了去除一些經常被認定的常規。因而在普遍的認知上,造就了某些被認為浪費的過程,然而對於他們來說,這樣的浪費卻是一種必須,也是必要的手段。尤其在此階段之後,更接續著改變與再造的程序。他們企圖改變作品施作的方式,並從中調整被觀看的視野,以及翻轉成果所賦予的意義。 袁慧莉的火墨利用材質轉換的方法,用燒製為過程,擷取物質消滅後的不滅之物:「炭」作為墨的使用。此時,殘缺變成作品另一個主體,這樣的過程其實也類似於礦物質經過人工研磨、消滅並化為原料的規則。換句話說,以炭為墨著重的是無用之物的再創造,這與她的水墨作品同樣都是摧毀了既定且完整的物件之後,再來作為重新編排,以及拼貼組合的意識。 黃柏皓則將單一材料重複使用,以規律的運作方式,凸顯創作者的無思狀態。此「無思」是將思考趨近於靜止,而此「靜止」則又歸咎於精神上,以及思緒上的平衡。對於他來說,「止」的動作也表現在作品上。相較於其他平面繪畫者而言,將紙張填滿色彩就像是初步的打底動作。但它還不能算是最終完成的結果。不過對於黃柏皓來說,適時的止步,變成了製作上的選擇。而他選擇在還沒有添加其他具象或抽象的形象時就此打住。作品這個時候改變了被運作的方式,最終就只剩下材料本身的獨語。由多層次的筆觸一次次填補到成為均質的色塊。色塊最終因為平面性而呈顯出「無」的狀態。如此試圖趨近與回歸原始的方法與「無思」的狀態,就在成果完成時達到了再生。 和黃柏皓類似使用「止」的意涵,曾霆羽卻是在磨墨的過程後就停止,以及改變了書寫與繪畫的後續。此時的磨墨是以觀念性的置入,利用制式的行為,用機器替代人力尋求一種消解形象的意志,作品裝置因而沒有一般繪畫的平面性與構圖元素。所以也就不介入顏料的偶發與碰撞展現,只在物質的探究裡,凸顯磨墨的過程在人文、歷史與社會的關係上互為對應。當改變形體過後的固體透過機械裝置成為了液態,墨的觀念性即成為他創作上所關注與再生的焦點。此時攸關於環境上的空汙、廢棄物、生態危機等等議題,就變成他加以改變與再造的材料。 物隨人用:提供生命另類可能的想像 作品實驗的方法往往能夠提供給觀者許多感官或知識上的刺激,尤其是對於歷史上既定法則的推翻,又或者給出了更多觀看世界的角度。三位創作者的作品所揭示出來的意義,同時也都反映出了他們各自面對社會,以及試圖提出思考材料使用時所面臨的困境,並依此改用其他種方式,尋求製造上的其他出口。甚至更進一步地,這些探索的過程,最終也都將會被類推成為,理解這個世界的取經路徑。 袁慧莉水墨與火墨的作品都因破壞而再生出另一種創作上的可能。尤其火墨的古畫新作,凸顯了當代社會所處的困境,此乃以渣回應理想境地的嘲諷,並且反應現下環境的困窘與不忍目睹之憾,利用往復的回歸找尋過往美好的境地。然而這個境地卻同樣被殘餘所建構。如此十足的嘲諷意味,凸顯了過往今來的種種矛盾。不僅是關於家園、環境、甚至是人的內心所憧憬的美好,都被其一一打破。而材料被重新使用後的創作,促使人們更深刻地思考該如何與自然更和諧地相處,也為活在這個備受汙染環境下的每一份子,注入些許反省思考的可能。 黃柏皓的平塗沒有材料跟材料碰撞上的偶發、交流與突發的狀況。顏料此刻獨自散發出自身的光彩,這乃是經過固態的顏料本身,再經過筆刷的繪製而鋪展到平面上的過程。但這意味著什麼?創作者以近似於徒然的刷洗過程尋找一種穩定且均勻的質地,其對應於這個繁雜而多元變動的社會,顯然具有某些個人精神性的探求。對於迷失在渾沌世界上的人而言,此樣沉靜的無思與「止」的方法,成為了另一種追求精神穩定的材料。或許,這也就是黃柏皓在他作品製作時所刻意提供給人生另一種探尋與追求的目標。 曾霆羽的機械裝置陳述了墨的物質,對應中國歷史長久以來的人文思考,也牽涉到了許多文化更迭的消長與過程。尤其在過往的東方世界中,墨跟讀書人的關係總離不開某種威權與精英式的場域。而西方工業的機械性,則打破了社會上下階層的藩籬。這代表著東西兩方物質的差異性,或許也就是曾霆羽試圖去衝撞與嫁接兩者的微妙關係。在南轅北轍的物質結構中,尋求歷史文化以及環境生態的共存,並依此提供出個人在思想上的寄望。 在理解了「物」將隨人所用的時刻,三位創作者不約而同都在物質的實驗過程中,表現出事物不應該受到既定規範的限制。也從過往的經驗中,再造出另一種材料使用的可能。最終,更藉此探索模式,提供給人生另類追尋的想像,以及勇於嘗試的冒險精神。 |